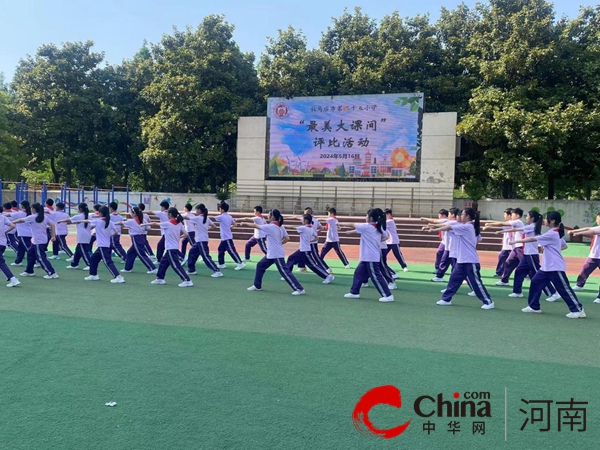吴刚,一级演员。主要话剧作品有《茶馆》《哗变》《北京人》《天下第一楼》《古玩》《阮玲玉》《风月无边》《日出》《合同婚姻》《北街南院》等。他凭借《铁人》获得第27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,凭借《人民的名义》获得第23届上海电视节白玉兰奖最佳男配角奖。影视作品还有《战狼Ⅱ》《破冰行动》《夺冠》《狂飙》《庆余年》等。
第23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期间,北京人民艺术剧院1个月内连上5部大戏。吴刚主演其中的《茶馆》《哗变》。
虽然已经62岁,吴刚依旧在观察生活,在随时思考。
“充电一定要充足。我在北京人艺跑了那么些年龙套,看先生们怎么演戏、怎么下功夫,给了我力量。”

每个角色都是摸着心演的
吴刚比同龄人瘦削,随时保持出镜的状态。围在上音歌剧院后门求签名的观众异口同声:“‘达康书记’竟然是大长腿。”
自律、用功、保持好奇心。在上海戏剧学院交流时,吴刚对上戏学生说,在校4年,如同上山拜师。“毕业后走向社会,是下山与别人比武。如果被打趴下了,你还得回山上接着练。”
55岁时,吴刚火出了圈,从达康书记到陈萍萍,“把一个角色演活了,这一类角色谁都演不过你,单看你怎么‘玩’”。
周末周刊:影视剧让更多观众认识您,您怎么看舞台与影视剧的关系?
吴刚:以前我们排话剧,准备两三个月开始演出,一场也就1000多名观众。现在你演影视剧,没准才一天全世界都知道你了,诱惑力是很大的。但是我们剧院还是要求演员必须坚守舞台,这是我们的主业。
我开始正经学习表演,就是在北京人艺。这个地方教会我做人和挣钱的本事。从老先生到新进剧院的青年演员,我们都把北京人艺当作自己的家。北京人艺每年底规划第二年演出,所有演出通知到灯光、服装、道具、化妆等各业务部门。你安排好第二年工作行程,剧院需要你登台,你必须准时报到。
周末周刊:《人民的名义》《破冰行动》《狂飙》等一部部拍下来,您经常演官员、警察,害怕被定型吗?
吴刚:看似都是公检法题材电视剧,实则角色背景、时代环境不太一样。故事有的发生在广东,有的在海外。今天我是刑警队队长,明天是公安厅厅长,案件、与同事关系都不一样。我抓捕的是企业家还是毒贩?我们俩认识多年,还是刚认识?我要套话,还是要抓你?都要把人物关系演明白。
《人民的名义》前,我见过最高职位的人就是我们剧院院长。当时我找了很多省市领导调研开会的视频,多感受,把人物关系捋清楚,就能演出差异化。
周末周刊:以前影视演员多是科班毕业,现在拿起手机就能拍,成了网红就有机会拍戏。
吴刚:时代在进步,但表演这件事,还得面对面教学。不像练书法,我请先生教,然后回家自己练。表演,你一个人在家怎么演?必须大家在一起,怎么排、怎么演,让老师给说说,几个人排好了,才能继续往下演。如果不用学,艺术院校都关门了。
周末周刊:您拍影视剧时,遇到过“独美”、只想秀自己的演员吗?
吴刚:我还真没见过这样的人。大家在一个剧组,三个月拍一个戏。影视剧是集体项目,导演拿主意,演员好好演自己的戏。没人会把戏往坏里演,都是尽一切努力把角色演好,才会有下一个机会。如果我在这个剧组嘚瑟,下一个机会可能就没了。想演独角戏,请回家自己对着镜子随便演。剧组讲究集体创作,我们拿的是团体分。
一部戏播出,大家都不喜欢其他演员,只喜欢你一个?不可能!剧作首先是打集体分,剧爆了,观众才有可能喜欢某个角色,点评“这哥们演得不错,那哥们稍微差点”。
周末周刊:影视剧播出后,您会看观众的评论吗?
吴刚:我有时候会看看评论。
我拍完一段戏,习惯现场看回放,觉得还行,这段戏就过了。我对所有角色都是100%全身心投入。每个角色我都是摸着心演的,然后交给市场评判。
拍影视剧,早上六七点钟开始化装,这一天不会停。一天十多场戏,所有台词必须记清楚,节奏很快。中午吃饭20分钟,最多半个小时。演话剧,白天排练,晚上自己消化。一部话剧一演就是10年,每年都在演。每场话剧都与昨天的不一样,更与去年的不一样。演员对人物不断有新的理解,表演一天天丰满。这个人物,你一辈子演下来,别人撼动不了你。
周末周刊:您认为,成为好演员有哪些必备要素?
吴刚:首先,天分要占一部分。我天分不高,有幸遇到北京人艺的先生们,与他们同台,这是福分。
我们在人艺学员班“滚”了两年,和林连昆、童弟、尚梦初等老师都是忘年交。那时候年轻人穷,老师说:小子,想抽烟了?这儿拿。我们也不客气,直接拿了烟,陪老师喝点酒,让老师多给我们讲讲戏,真是一种福分。
好演员的要素还有一点,那就是努力,努力是应该的。
周末周刊:除了演戏,您平时忙什么?
吴刚:看书,出去走一走。
我今年夏天去了英国,看西区驻场音乐剧,场场爆满。除了游客对戏剧好奇,还有很多观众反复看这些剧。为什么?你要走出去,自己看一看,学习同行对表演、对戏剧的理解,看看博物馆,听听音乐会。“读万卷书,行万里路”是有道理的。演员肚子里没货,没法引领观众。
周末周刊:您喜欢看什么样的书?
吴刚:专业类书籍看着看着就开始看烦了。我喜欢看人物传记,了解人物发展脉络,帮助塑造角色。韩国作家拿了今年诺贝尔文学奖,我也下载了她的电子书,正在看。她为什么能获奖,咱们得学习学习。另外,所有获奖影片,我基本上都看。
学习无处不在。艺术要高于生活,首先得源于生活,瞎编不行。买菜做饭,逛街会朋友,这也是我的生活常态。我们小区里,大家都认识,见了面都会相互打招呼。
在台上永远得提着一口气
10岁时,吴刚考入银河少年艺术团。长大后,他做过两年警察。
1985年,北京人艺表演培训班从3000多名报名者中录取15名学员,两年后8人毕业,包括吴刚与他未来的妻子岳秀清。
同学冯远征对班长吴刚练功记忆犹新:“吴刚20多岁才开始练开胯。每天出晨功,同学把他摁在墙上,两边扳着他的腿。吴刚痛得叫唤,还在坚持。”
周末周刊:您年轻时对做话剧演员有过踌躇吗?
吴刚:没有。那时候先生们都是这样,全熏在戏里。
我们排戏一整天,都不愿走。边上有一饭馆,我们请先生们一块儿继续聊戏,过瘾。我们年轻人排了一段戏,先让先生看看。先生说你这儿稍微差点,再感觉感觉。第二天接着改,稍微有点进步了,我就高兴坏了。
演戏得全身心投入,体力劳动加脑力劳动,很累。我在《雷雨》里演周萍,一场戏下来,真要虚脱了。
在台上永远得提着一口气,精神不能有丝毫闪失。人的思维是活跃的、跳跃的。比方说,我和你聊天,你听我说话,某个瞬间你可能会想到“等会儿得去买点菜”。演员也会这样。在舞台上如果思维散发开,瞬间就得把它抓回来,否则就完蛋了。
周末周刊:您有特别想挑战的角色吗?
吴刚:无论话剧还是影视剧,我都特别希望演一些没有接触过的类型。演员怕被固定在一个类型。当然,人都有局限性,我们看看能不能大胆突破一下。人艺45岁以下演员每年有年度考核,演员可以自选题材,想演王昭君、想演王利发,都可以。给演员最大的空间去尝试,这是对年轻人的锻炼,看看他们有没有更强的角色塑造能力。
剧院每年演出剧目、场次就这么多,很多演员想登台,但没机会。怎么办?那就在考核中拿出真水平。考官一看,说“明天吴刚别演了,换人演”,这都有可能。
周末周刊:您在北京人艺最早演出的剧目是什么?需要竞争上岗吗?
吴刚:学员班毕业后,我最早演的台词比较多的角色是《天下第一楼》里的孟四爷,那也是我们剧院的保留剧目。我演完孟四爷,再在剧里跑俩龙套,一晚演两三个角色,真的挺锻炼人。
北京人艺有导演和前辈艺术家组成的艺委会,确定演员名单。《茶馆》就是这样。剧院宣布复排《茶馆》时,所有演员期盼已久,等着哪天宣布谁在《茶馆》里演哪个角色。
周末周刊:您和妻子都是北京人艺85级表演培训班学员,平时在家聊戏吗?
吴刚:聊!从年轻时一直聊到现在。比如演《茶馆》前,我们在家先遛遛词,每年如此。虽然词儿比较熟,但是你重新看一遍剧本,可能有新的认识,这也是《茶馆》是北京人艺镇院之宝的原因。我去年演《茶馆》没有悟到的感觉,今年突然找到了,角色塑造又能有提升。
周末周刊:这几年北京人艺恢复表演培训班,您有没有去上课?
吴刚:岳秀清当了班主任,出于情分,我得给她开个车吧。她教学生累着了,我得去看看,也跟学生们聊聊。剧院是一个家,家里边有点什么事儿,必须全力以赴。北京人艺每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。
周末周刊:什么样的人可以通过表演培训班进入北京人艺?
吴刚:近年的两届演员培训班都是全国招生。岳秀清带的班大部分是刚毕业的学生。最近一个班,我们对年龄段放宽了,有影视剧、话剧表演经验的人,也能到我们剧院回炉。一年学习结束后有甄别,您是很优秀的演员,但不适合北京人艺,可能就进不来。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,我们剧院都得有。打个比方,如果这回就想招几个小生,您是花脸,戏再好,我们这儿有三个花脸,您可能就得去其他地方试试。
周末周刊:现在年轻演员面临的竞争,比您入行时更大吗?
吴刚:我们那时影视剧拍摄机会不多,进了剧院,一门心思跟先生们演话剧。北京人艺只有一个剧场,后来慢慢多了一个小剧场,现在有4个剧场。剧场多了,竞争压力也大。你的表演是不是受欢迎,戏是不是叫座,全靠真功夫。不过,现在影视剧也多,年轻演员有机会出去锻炼,这是他们的优势。
老想着面子,这剧怎么出彩
北京人艺从1958年开始以团带班的形式培养演员,年轻演员和家里的孩子一样,和“大人”一块生活、学习、巡演。
吴刚还记得,1988年坐着火车来上海演出,每个年轻演员负责一位老先生,他被分配到夏淳导演。老先生们岁数大了,年轻人帮着提行李。后台黑漆漆的,年轻人给他们登台前扶把手。
谢幕后,大家聊的还是戏:今天这场戏,你接词慢了一点,明天还得恢复以前的节奏。“现在我们下台后还是这么聊,已经成了习惯,都尽可能让戏更完善、丰满。”
周末周刊:这一个月,北京人艺再次来上海驻演,在上音歌剧院连演五部大戏。
吴刚:上音歌剧院真挺棒,非常能聚拢演员的声音。北京人艺有习惯,演员表演时不戴麦克风,全靠自己说词,把台词“打”到最后一排观众。北京人艺所在的首都剧场有900多个座位,上音歌剧院有1200座,我们在北京还有些担心。远征和《茶馆》复排导演杨立新、技术团队提前来看台,说声音很棒,完全不用担心。事实的确如此。
周末周刊:这是焦菊隐版《茶馆》时隔36年来到上海。
吴刚:我们从培训班一毕业,就跟着《茶馆》剧组。1988年,北京人艺五个戏来上海,于是之、郑榕、蓝天野等老先生们带着我们。那时候我们还小,都跑龙套。我们班唯一有台词的演员是我媳妇岳秀清。她演小丁宝,与先生们有面对面的接触。其他人都演群众,甲乙丙丁,在舞台上一晃就过去了。
老先生们排练,场地非常安静。导演席摆着一个钟,只要一敲钟,大家鸦雀无声。我们在边上静静地看先生怎么塑造人物。那是一段非常幸福的时光。老先生们的博学、对舞台的掌控、对戏剧艺术的追求与热爱,太浓烈了。
1999年,我们这代演员接过《茶馆》。对每段台词,大家都一起想办法。于先生那代人经历过《茶馆》的年代,我们离那个年代有点距离,怎么追上?大家讨论戏完全没有“遮挡”,演得不好就是不好,明天必须改;接词接得不对,为什么不对?哥几个一块聊这事儿,得聊透了,把问题彻底解决。直到现在,我们依旧互相对表演提出建议,比如“你这段刚才接晚了,在想什么呢”,都是直说。家里人说话就这样,不能拘着面子。老想着面子,这剧怎么出彩?
周末周刊:您这次演的另一出戏《哗变》,与《茶馆》相比,风格又是一变。
吴刚:感谢北京人艺的前辈艺术家,他们真正具有前瞻性眼光。英若诚先生亲自翻译剧本,把《哗变》引到中国。剧院请电影《宾虚》的主演、奥斯卡最佳男主角查尔顿·赫斯顿担任导演,他也演过《哗变》。那是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。
我们观察外国演员在舞台上怎么演戏,戏剧理论是不是相通,搁在中国舞台上是不是可行。《哗变》舞台调度别具一格,全程只有辩护律师格林渥在走动,其他角色如证人、陪审团都坐着,靠台词塑造人物,非常契合北京人艺。“话剧姓话”,演员得把话说清楚,让观众听明白。
《哗变》排演,提前一个多月集结剧院中青年演员,朱旭老师饰演凯恩舰舰长魁格,任宝贤老师饰演辩护律师格林渥,那真不得了。排《哗变》时,美国驻中国大使夫人到现场看,把鞋脱掉,光着脚走进去,怕影响演员状态。我们都是趴在门缝里头看,不敢打扰先生们。
周末周刊:您是如何与《哗变》结缘的呢?
吴刚:扮演凯恩舰哗变者、被告马瑞克的演员临时有事,导演让我顶上。我有幸和朱旭老师、任宝贤老师同台演戏。我第一次演《哗变》在首都剧场,很紧张。任宝贤老师饰演律师,第一个上台,我是第二个。候场时,任老师突然拍了我一下,“小子别紧张,放松”。他的鼓励真的让我不紧张了。
有一轮《哗变》演出前,任宝贤老师突然失声,票已卖出去。剧院说,吴刚你赶快准备,顶替任老师演律师。任鸣导演帮忙排了一个星期,我把格林渥的台词全记下来了,这时宝贤老师声音又突然好了,可以继续演出了。
格林渥是《哗变》的灵魂人物,整个戏节奏由他来掌控,对演员有极大的锻炼。那次没演成,我就一直想演这个角色。
2006年《哗变》复排,先生们年龄大了。人艺前任院长、任鸣导演给我打电话,想恢复《哗变》。我说太好了,我只有一个要求,想演辩护律师格林渥,如果演不了这个角色,我就不参加了。现在回想,我那时候胆子也挺大,敢跟领导提要求。后来我如愿以偿,一直演到现在。
周末周刊:您的《哗变》与上一代相比有什么特色?
吴刚:导演要求我们上台要精神、要帅,与先生们同台演出时,要发挥我们的主观能动性。因为是你在诠释这个角色,每个人对角色都要有自己的理解。
《哗变》的难点在于台词环环相扣,逻辑性极强,有一句台词说错了,后边剧情就圆不上。每个演员上台,一直说说说,接着律师对每个人开始提问。对象不一样,律师的提问也不一样。今天排格林渥和马瑞克两个人的戏,明天排格林渥和魁格两个人的戏。一天结束,头昏脑涨,得慢慢消化。两个多月排练,每天琢磨戏。
现在一些青年演员扮演剧中的陪审员、法官,他们上台感受《哗变》,了解应该怎么演,与我们刚毕业时候看先生们演戏,其实是一个道理。
周末周刊:您演完《茶馆》,接着演《哗变》,连轴转,感觉如何?
吴刚:现在环境太“躁”了,演戏,还是要静下心。
我习惯下午休息,保证晚上演出状态。北京人艺演出队要求演员下午五点半到后台。很多演员四点半、五点就陆陆续续到了。我们在北京演出也是这样,养成了习惯。
晚上七点半演出,我们基本五点就到了。大家沏杯茶,聊一聊,开始化装。一点点化装,在这个过程中慢慢进入人物。从老先生们开始,我们剧院都是这样。我们学着先生这点习惯,没有啥规定,成了大家不约而同的流程。
周末周刊:北京人艺今年72岁了,今后发展有哪些规划?
吴刚:时代在发展,一定要跟上时代潮流。我们剧院每年请国外优秀剧目来北京参加展演,我们也会研究国外同行的戏剧。
我们排演了不少新剧本。北京人艺现在有4个剧场同时开锣,有实验性剧目、优秀引进剧目。在与观众近距离的交流中,我们不断尝试探索,去应对时代的选择。同时,我们还要排演自己的优秀保留剧目,这对演员而言是一种学习,也是对剧院传统的一种传承。